王賡武:人類必須設法維持和平環境,才能避免自我毀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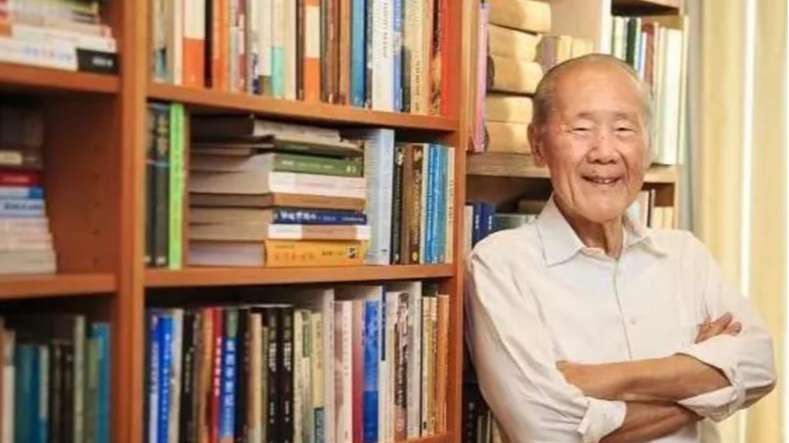
王賡武:人類必須設法維持和平環境,才能避免自我毀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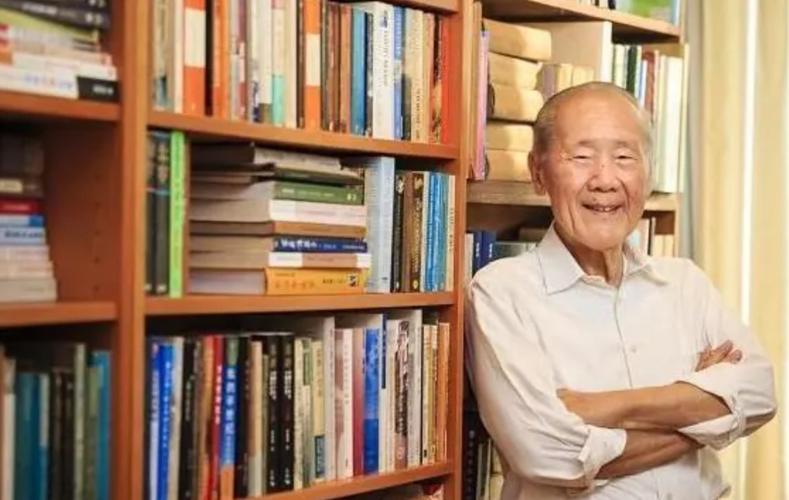
享譽世界的歷史學家王賡武教授年近期頤,這位95歲的學者仍筆耕不輟,思想敏銳。近日,他還接受了媒體專訪,我們在此還原該次專訪的核心內容,呈現王教授對當今世界局勢、文明衝突及中國現代性等議題的深刻洞見。
王賡武教授1930年出生於荷屬東印度(今印尼),幼年隨父母移居英屬馬來亞。其早年教育橫跨中西:1947年,他考入南京國立中央大學,親身感受故國的脈動;翌年,因時局動蕩,轉入新加坡馬來亞大學歷史系。這段經歷為他日後獨特的雙重視角埋下伏筆。
為求深造,王教授遠赴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後移民澳洲,在學術界嶄露頭角,出任澳洲國立大學遠東歷史系主任。1968年,他受國際漢學泰斗費正清之邀撰寫的《明初與東南亞關係》論文,被盛讚為「大師之作」,史學大師錢穆亦鼓勵其從外部視角深入研究中國歷史。
他的學術生涯與教育事業並行。1986年至1995年,王教授出任香港大學校長,在此期間,他將研究視野從早期的五代史、南海貿易,拓展至更為宏大的中國現代化進程。卸任後,他於1996年起擔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所主席及東亞研究所所長,繼續為學界貢獻心力。
王賡武教授與余英時、許倬雲齊名,並稱為「海外華人史學三大師」。其跨越怡保、南京、新加坡、倫敦、香港等多城的生命體驗,賦予了他對文明、民族與國家變遷的獨到洞見,使其成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華人學者之一。
新著問世:《中國現代性之路》
在訪談之際,王賡武教授的新著《中國現代性之路:文明與民族文化》亦於新加坡出版發行。該書以其標誌性的海外華人學者雙重視角,深入解構了中國從一個古老、無邊界的「天下」文明,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複雜歷程。
核心觀點一:釐清「文明」與「文化」 王教授指出,傳統華夏文明的「道統」或「天下」觀念,本質上不具備邊界意識。而現代國家文化,則是在西方民族國家概念引入後,才與明確的疆界掛鉤。這一轉變,是理解中國現代性挑戰的關鍵。
核心觀點二:闡釋「多元一體」 他認為,中國的國家認同既建立在統一的政治框架之上,又包容着豐富的文化差異,不能簡單套用西方單一民族國家的模式來理解。該書旨在思考當今中國面臨的持久挑戰:如何構建一種既能接納全球思想,又能保持鮮明中國特色的現代民族文化。
專訪核心論述
一、 關於中美關係:是「富強」之爭,非「文明」之辯
當被問及文明差異是否為影響中美關係的根本原因時,王教授明確表示,文明差異有影響,但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富強」。他認為,任何大國對富強的追求,都會產生控制世界經濟與政治的願望。當中國富強了,美國自然會視之為威脅並試圖遏制。這種對立已經與文明文化無關,演變成了純粹的國力較量。他形容這是一種「非常可怕的現象」。
二、 關於全球化與民粹主義:自由主義的失敗與反彈
王教授認為,二戰後建立的聯合國體系承載着人類的崇高理想。但冷戰後,美國錯誤地將其模式的自由主義視為「歷史終結」,並試圖將其普世化,最終因實力不逮而失敗。這種失敗直接引發了美國本土的民粹主義反彈。他指出,當民眾看到日益擴大的不公時,民粹主義便成為一條必經之路,其本質是對現有統治權力的反抗。
三、 關於歷史與邊界:人為建構與和平的必要性
在談及歷史被「武器化」時,王教授指出,民族國家的永恆歷史邊界,更多是人為建構的想像。歐洲許多國家的邊界都非常新近,充滿爭議。他強調,亞洲國家對此缺乏經驗,必須格外謹慎。因為亞洲多數國家的邊界是近百年才劃定,且普遍存在模糊性。若對邊界採取絕對化立場,必然引發災難。因此,各國需要相互尊重現有邊界,探索和平共處的路徑。
四、 對年輕一代的建議:在科技革命中追求和平
面對當今世界的動盪與科技的飛速發展,王教授向年輕一代提出了一個強烈的希望:人類必須設法維持和平環境,才能避免自我毀滅。他認為,當今科技賦予了人類過強的毀滅力。因此,我們必須尋找新的思想體系,來幫助人類減少鬥爭的本能,避免那些企圖利用科技挑起衝突的行為。他最後表示,相信人類追求生存的天性,本身就是希望的源泉。
圖文素材:澎湃新聞
王賡武:人類必須設法維持和平環境,才能避免自我毀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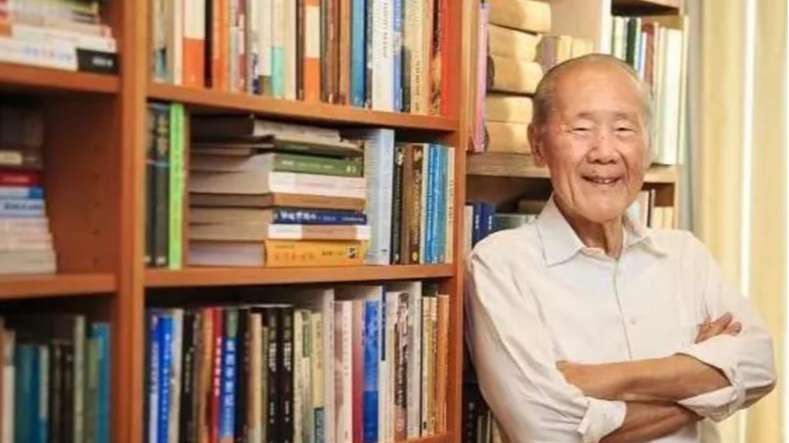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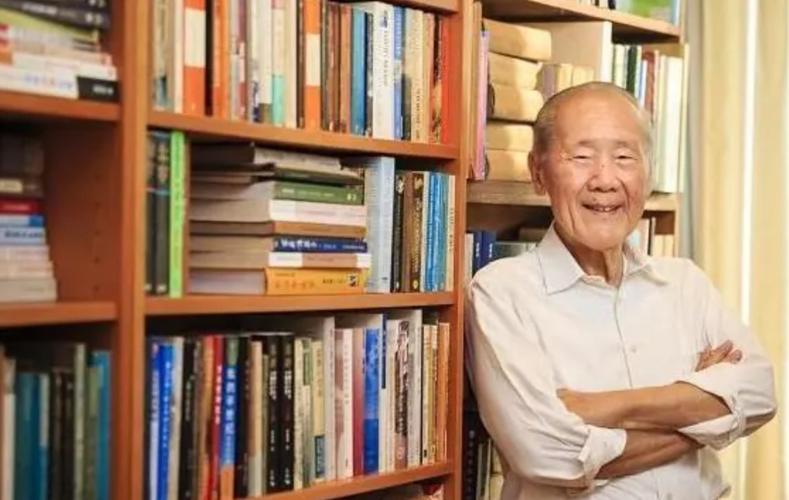
享譽世界的歷史學家王賡武教授年近期頤,這位95歲的學者仍筆耕不輟,思想敏銳。近日,他還接受了媒體專訪,我們在此還原該次專訪的核心內容,呈現王教授對當今世界局勢、文明衝突及中國現代性等議題的深刻洞見。
王賡武教授1930年出生於荷屬東印度(今印尼),幼年隨父母移居英屬馬來亞。其早年教育橫跨中西:1947年,他考入南京國立中央大學,親身感受故國的脈動;翌年,因時局動蕩,轉入新加坡馬來亞大學歷史系。這段經歷為他日後獨特的雙重視角埋下伏筆。
為求深造,王教授遠赴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後移民澳洲,在學術界嶄露頭角,出任澳洲國立大學遠東歷史系主任。1968年,他受國際漢學泰斗費正清之邀撰寫的《明初與東南亞關係》論文,被盛讚為「大師之作」,史學大師錢穆亦鼓勵其從外部視角深入研究中國歷史。
他的學術生涯與教育事業並行。1986年至1995年,王教授出任香港大學校長,在此期間,他將研究視野從早期的五代史、南海貿易,拓展至更為宏大的中國現代化進程。卸任後,他於1996年起擔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所主席及東亞研究所所長,繼續為學界貢獻心力。
王賡武教授與余英時、許倬雲齊名,並稱為「海外華人史學三大師」。其跨越怡保、南京、新加坡、倫敦、香港等多城的生命體驗,賦予了他對文明、民族與國家變遷的獨到洞見,使其成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華人學者之一。
新著問世:《中國現代性之路》
在訪談之際,王賡武教授的新著《中國現代性之路:文明與民族文化》亦於新加坡出版發行。該書以其標誌性的海外華人學者雙重視角,深入解構了中國從一個古老、無邊界的「天下」文明,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複雜歷程。
核心觀點一:釐清「文明」與「文化」 王教授指出,傳統華夏文明的「道統」或「天下」觀念,本質上不具備邊界意識。而現代國家文化,則是在西方民族國家概念引入後,才與明確的疆界掛鉤。這一轉變,是理解中國現代性挑戰的關鍵。
核心觀點二:闡釋「多元一體」 他認為,中國的國家認同既建立在統一的政治框架之上,又包容着豐富的文化差異,不能簡單套用西方單一民族國家的模式來理解。該書旨在思考當今中國面臨的持久挑戰:如何構建一種既能接納全球思想,又能保持鮮明中國特色的現代民族文化。
專訪核心論述
一、 關於中美關係:是「富強」之爭,非「文明」之辯
當被問及文明差異是否為影響中美關係的根本原因時,王教授明確表示,文明差異有影響,但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富強」。他認為,任何大國對富強的追求,都會產生控制世界經濟與政治的願望。當中國富強了,美國自然會視之為威脅並試圖遏制。這種對立已經與文明文化無關,演變成了純粹的國力較量。他形容這是一種「非常可怕的現象」。
二、 關於全球化與民粹主義:自由主義的失敗與反彈
王教授認為,二戰後建立的聯合國體系承載着人類的崇高理想。但冷戰後,美國錯誤地將其模式的自由主義視為「歷史終結」,並試圖將其普世化,最終因實力不逮而失敗。這種失敗直接引發了美國本土的民粹主義反彈。他指出,當民眾看到日益擴大的不公時,民粹主義便成為一條必經之路,其本質是對現有統治權力的反抗。
三、 關於歷史與邊界:人為建構與和平的必要性
在談及歷史被「武器化」時,王教授指出,民族國家的永恆歷史邊界,更多是人為建構的想像。歐洲許多國家的邊界都非常新近,充滿爭議。他強調,亞洲國家對此缺乏經驗,必須格外謹慎。因為亞洲多數國家的邊界是近百年才劃定,且普遍存在模糊性。若對邊界採取絕對化立場,必然引發災難。因此,各國需要相互尊重現有邊界,探索和平共處的路徑。
四、 對年輕一代的建議:在科技革命中追求和平
面對當今世界的動盪與科技的飛速發展,王教授向年輕一代提出了一個強烈的希望:人類必須設法維持和平環境,才能避免自我毀滅。他認為,當今科技賦予了人類過強的毀滅力。因此,我們必須尋找新的思想體系,來幫助人類減少鬥爭的本能,避免那些企圖利用科技挑起衝突的行為。他最後表示,相信人類追求生存的天性,本身就是希望的源泉。
圖文素材:澎湃新聞



























